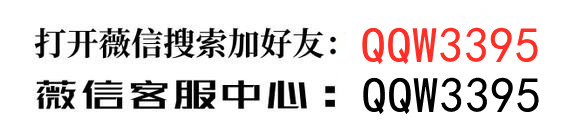

直到几年前,格雷·威尔逊(Grey Wilson)作为一名跨性别者的旅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平静的。
在他13岁生日的前一周,他向他的母亲劳伦(Lauren)做了一个ppt演示,阐述了为什么他应该被允许变性。这在之前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方法:每次他想收养一只狗或兔子时,他都会制作一个幻灯片,详细说明养宠物的成本、适当的喂养时间表,以及在哪里可以得到他想要的动物。(格雷只在向劳伦要一条蛇时被拒绝了。)
劳伦自称是一个数据迷,她发现自己被格雷汇编的关于性别肯定的心理好处的研究说服了。当演讲结束时,她对自己说:“是的,那是我儿子。”
但格雷的幸福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结束了,他在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作证,反对2021年一项旨在禁止未成年人性别肯定护理的法案。在他们的家庭地址在网上被分享后,反跨性别活动人士出现在她家门口。劳伦说,当她开车时,一些拿着突击步枪的男子尾随她,并试图跟着她去上班。格雷突然被一种新的内疚所困扰,他害怕自己把这一切都强加给了自己。“他们恨她的是我,"他心里想。“他们追她是因为我。”
“我觉得自己对发生的事情负有很大的责任,”现年19岁的格雷说。“我知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的,但我的一部分想法是,‘好吧,如果我不是变性人,她就不会受到骚扰了。’”
在格雷作证两年后,禁止为德州青少年提供性别确认护理的法案成为法律,该法案威胁到为未成年人提供过渡护理的医生将失去执照,许多家庭因此离开了该州。但出于安全考虑,威尔逊夫妇没有透露他们的真实姓氏,他们担心,仅仅去加州或科罗拉多州这样的蓝州是不够的。如果他们的新州开始通过与旧州相同的政策怎么办?劳伦知道卖掉房子所产生的收入只够支付一次搬家的费用,她担心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州,他们就会陷入困境。
格雷和劳伦没有冒着唯一的逃跑机会的风险,而是决定逃离美国,在新西兰重新开始——在这个国家,他们几乎没有朋友或关系。他们选择新西兰是出于务实的原因:新西兰被认为是世界上对LGBTQ+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智库威廉姆斯研究所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排名第十,而且气候比排名第五的加拿大更温和。他们不需要学习一门新语言,不像第三名挪威和第十一名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爬行动物种类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这是劳伦的主要障碍。(相比之下,新西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蛇的国家。)


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学校和填写学生签证文件的过程,格雷进入了奥克兰一所大学的护理课程,劳伦被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录取。今年2月,格雷终于独自登上了一架飞机,准备在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他的母亲在解决了他们的事务,包括离婚后,也会跟着他去。她的前男友除了被派往伊拉克之外很少离开德克萨斯州,他在搬家前不久告诉她,他无法让自己离开。
今年早些时候,当他走下飞机时,他期待着来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新地方,他终于可以自由了。相反,突然意识到最糟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这实际上出乎意料地令人难以承受,他幸存下来的事实使他几个月来压抑的所有情绪重新浮现出来。然后他想起了劳伦在骚扰最严重的时候告诉他的话: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格雷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美国,完成他们的计划。
他说:“我们一年前想到的这个东西正在发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担心我不能上飞机,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很担心我下车后,他们会拒绝我。我担心一切都会出问题。”
一些跨性别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逃离美国——因为美国各地的立法者对性别确认医疗保健施加了越来越严厉的限制。迄今为止,已有20个州通过了法律,限制医生开青春期阻断剂、提供激素替代疗法(HRT)和对未成年患者进行手术,亚利桑那州有一项法律只适用于性别确认手术(只有在极端医疗需求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实施)。佛罗里达州的性别确认护理禁令甚至允许法院在当局得知孩子正在变性的情况下将孩子从家中带走,反对者称这一规定相当于合法绑架。
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的家庭认为,离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在2024年总统大选迫在眉睫之际。共和党提名的几位候选人,包括前美国大使尼基·黑利和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都公开反对允许变性儿童在18岁之前获得性别确认护理。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呼吁联邦政府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变性治疗,其中包括现任共和党领跑者、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将变性青少年的医疗保健比作“虐待儿童”和“残缺儿童性器官”。
格雷知道,他的家人很荣幸能够收拾一切搬家,但当他想起他们留在德克萨斯州的朋友和社区时,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就会卷土重来。但在他的新公寓里,他通过Zoom的电话说,在一个剥夺他基本权利的国家,在一个他作为自己生活的机会正在缩小的国家,他没有未来。
他说:“我们真的不太希望情况在明显恶化之前会好转。”“我们宁愿不必处理更糟糕的部分。”
目前还不清楚美国还有多少家庭因为歧视性政策而选择移居国外,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任何资源或基础设施支持。致力于倡导LGBTQ+移民的非营利组织——比如美国的“移民平等”组织和加拿大的“彩虹铁路”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从全球南方移民到北美的难民。变性人和他们所爱的人走向相反的方向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TRANSport是为数不多的为寻求与家人一起离开美国的跨性别美国人提供专门资源的组织之一。TRANSport是一家总部位于北达科他州的组织,由莱恩·阿泽里亚·威尔戈斯创立。该组织正在申请正式的非营利地位,旨在从达科他州和邻近的明尼苏达州重新安置。今年1月,当她接受VICE新闻采访时,威尔戈斯报道说,已经有30人寻求帮助,希望移居国外。Willgohs没有回应对这个故事的评论请求,但请求的数量可能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大幅增加:根据LGBTQ+智库运动进步项目提供的数据,2023年已经提出了700多项反LGBTQ+法案,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多的。
离开美国的跨性别青年的家庭可能需要尽可能多的帮助:移居国外是一个耗时、耗费情感的过程,通常要花费数万美元。Sirelo是一个独立的在线平台,可以让客户评估搬家公司。该平台估计,搬到新西兰的成本在1.5万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例如,为了找工作而搬到新西兰的工人,将需要申请一种众所周知的昂贵的从工作到居住的签证,费用接近2,000美元。劳伦和格雷发现,在新西兰,要找到能容纳四只猫和三只狗的住所是极其困难的;许多房东要求他们提交一份“狗简历”,详细说明他们的品种和各自的性情。
如果没有现成的关系网,跨性别儿童和他们的亲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无论是寻找友好的国家,还是为他们的搬迁提供资金。2021年11月,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连任后,玛丽·庞塞(Marie Ponce)一家决定搬到乌拉圭,他们知道自己负担不起把四居室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带走的费用——一家国际存储服务公司的在线计算器估计,这将花费高达1.7万美元。
当玛丽、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下个月离开美国时,他们将只带四个手提箱。一位朋友同意保留他们的汽车和一些家庭相册,以确保他们过去的生活留下一些记录,他们花了几年时间在德克萨斯州建立的生活。
出于安全考虑,庞塞夫妇选择了搬到乌拉圭,尽管费用很高,玛丽说,因为乌拉圭是南美洲最欢迎外国工人的国家之一,他们可以在三年后获得居留权。乌拉圭也有一些世界上最进步的法律,要求跨性别群体享有平等权利。在2009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跨性别者在政府文件中更正自己的姓名和性别认同后,该国在2018年更进一步,制定了旨在保障“没有歧视和污名化的生活”的全面政策。通俗地说,“跨性别法”确立了性别确认护理的宪法权利,并为跨性别工作者预留了1%的政府工作岗位。
他们希望在乌拉圭找到一个地方,让玛丽9岁的女儿克洛伊(Chloe)不再是一个政治足球。在德克萨斯州通过性别确认护理禁令之前,雅培于2022年2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德克萨斯州家庭和保护服务部调查允许孩子变性的父母。该指令实现了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整整一年来一直试图做的事情:2021年4月,立法者推进了一项立法,试图将向未成年人提供性别确认护理归类为“虐待儿童”,这在德克萨斯州可能是一项一级重罪,最高可判处99年监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儿童福利机构对全州几十个家庭展开了调查,庞塞夫妇整理了一个“安全文件夹”,里面有来自家庭成员、心理学家甚至当地宗教领袖的信,这些信都说克洛伊很快乐、很健康,以防有人来敲门。玛丽知道这不是她孩子的生活方式,克洛伊需要生活在一个不再害怕被迫害的地方。
“让我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玛丽说。“我试着让她远离外界,这样她就能长大,做她自己。如果你了解她,她最没意思的事就是她是变性人。我只是想去一个人们不会在意的地方。”

目前关于美国移民的数据很少,但现有的少量研究表明,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可能会有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家庭跟随庞塞夫妇和威尔逊夫妇的脚步。在自由派智库“进步数据”(Data for Progress) 6月份的一份报告中,41%的跨性别成年人和43%的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表示,由于反lgbtq +的立法,他们考虑过搬家,无论是搬到另一个州,还是干脆离开这个国家。这项对1036名受访者进行的全国调查发现,8%的跨性别成年人已经离开了家,因为政策使他们的自由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仅仅因为跨性别者和他们的家人可以搬家,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容易的选择。玛丽试图让孩子们相信这次搬家是一次冒险,是一个让他们看到世界的机会,但她内心深处知道,这并不是她想要的。自从她的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玛丽就梦想着他们会在她所谓的“终身社区”中成长,他们会在小时候抱过他们的叔叔、阿姨、邻居和做礼拜的人的陪伴下长大。
“我是在一个小镇上长大的,”玛丽在她说话时断断续续的电话线上说。“他们奉献的教堂——他们点燃圣餐杯并认识所有小老太太的地方——他们将失去这些。重建它真的很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重生。你不会再像个婴儿一样长高了。那绝对是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跨性别移民走出美国变得越来越普遍,事实仍然是,对于美国LGBTQ+社区目前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来没有一个已知的跨性别美国人以政治迫害为理由在国外申请庇护的案例,而那些确实移民的人可能会在允许他们在哪里和如何工作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例如,一些国家不允许移民在申请公民身份时就业。即使是那些获得学生签证的人,比如威尔逊夫妇,或者依赖远程工作的人,比如庞塞夫妇,如果突然失业,也会非常脆弱。
第三位接受采访的家长瓦妮莎·尼科尔斯(Vanessa Nichols)意外被哥斯达黎加旅游部门解雇,她被迫将14岁的儿子从哥斯达黎加接回美国。她和她的儿子最初于2020年11月逃离佛罗里达州,因为他们开始收到死亡威胁,其中包括一封手写的便条,告诉她如果她不为儿子的身份“忏悔”,她将被当地暴徒追捕。
“感觉很可怕。它感到孤独。在得知自己被解雇前几天,尼科尔斯在Zoom的电话中说:“我觉得不可能一直处于那种状态,因为那不安全。”“我是芝加哥人,但在我10岁的时候,我父母把我搬到了佛罗里达,所以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突然间,我觉得很陌生。”
对于那些负担不起移民费用或不想冒险搬迁到那些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缺乏支持网络的国家的家庭,新兴团体正在帮助跨性别者及其亲属在美国找到安全的避风港和其他他们需要的资源——包括建议LGBTQ+肯定学校,帮助家庭找到医疗保健。这类组织包括“高架通道”(Elevated Access),这是一种门到门的直升机服务,帮助跨性别乘客飞出州,重新安置或寻求性别确认护理;过渡司法,为寻求离开敌对国家的跨性别者提供住房;玛莎的地方,专注于为那些专门想搬到拉斯维加斯的人寻找安全的住所。
明尼苏达州成立了一个倡导团体联盟,以满足搬到该州的跨性别移民的需求。明尼苏达州是美国正式宣布自己为跨性别医疗保健避难所的十几个州之一。但社区组织正在争先恐后地满足面临前所未有危机的人口的需求:根据LGBTQ+非营利组织转变明尼苏达州家庭的数据,至少有60个家庭已经搬到该州或确认他们打算这样做。该组织执行董事汉娜·爱德华兹(Hannah Edwards)表示,该组织每周都会收到“两到三封”来自家长的电子邮件,寻求帮助以确保安全。
由于这一小部分团体所能帮助的客户数量严重有限,尤其是因为许多组织仍处于试点阶段,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变性人往往被迫开辟地下通道以获得安全。
罗伯托·切·埃斯皮诺萨(Roberto Che Espinoza)和他的伴侣今年逃离了田纳西州,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右翼组织长达数年的有针对性的骚扰,埃斯皮诺萨说,这些骚扰包括寄到他们家的没有标记的包裹。在他搬家之后,埃斯皮诺萨的非营利组织“我们的集体成为”(Our Collective Becoming)转向为搬到大罗切斯特地区的跨性别者和家庭提供互助基金,他目前住在那里的一所安全的房子里。他估计,他们所在的纽约州北部地区“每个月接待100到200名跨性别和酷儿难民”。
埃斯皮诺萨正在努力让当地教堂在变性难民和他们的亲人重新定居时捐赠食物、衣服,甚至是钱。“住房是一个很大的需求,”他说。“罗切斯特没有房租管制,人们确实需要经济适用房。没有足够的精神卫生保健提供者,而且随着这些人的涌入,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在新西兰的新家,威尔逊夫妇还希望为那些不确定应该留在美国还是尽快离开的跨性别人士和家庭创造一个安全的通道,他们甚至可能不确定自己会去哪里。他们目前正在申请庇护,如果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们将成为第一批因跨性别身份而在国外获得难民身份的美国人。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案件何时会得到判决。
当他们等待法律诉讼的消息时,格雷正在适应新西兰的生活,无论是辩证英语中的语法细微差别,还是学习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毛利词汇的意思。他也在适应当地的食物:在奥克兰,唯一能买到酸黄瓜的地方是一家卖美国食物的杂货店。他说,披萨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新西兰流行起来,披萨通常包括“各种各样的随机配料”。还有一个问题是新西兰的两种口味的牛奶,包括香蕉味、薄荷味和酸橙味,他拒绝尝试后者。“我不会测试这种组合,”他自信地说。
对劳伦来说,调整的过程更加艰难,因为她们为了取得现在的成绩牺牲了一切。她为了支付搬家费用而卖掉的房子是她梦想中的房子,是她应该在里面度过晚年的房子,她想念那里的古董木地板。她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好工作,在她最终于6月离开美国后,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以一名持学生签证寻找兼职工作的外国工人的身份找到了工作。
劳伦知道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当她睡在新公寓地板上的床垫上时,她忍不住为他们失去的东西感到悲伤。
“我儿子很开心,”她说。“他正在茁壮成长。不是我不开心,而是我放弃了生活中的一大部分,我不能再回去了。我们真的很幸运,我们能够负担得起这样做,并且我们安全到达了,但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